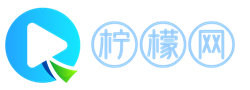我不记得兔子为什么被叫做“兔子”——就像很多人叫我“唐小六”,但并不知道为什么。外号叫得多了,本来的名字倒被遗忘了。
兔子这人本身跟兔子没半毛钱关系。他长着一张国字脸,眼神涣散,永远缺乏睡眠;他个子高,块头也大,很是虎背熊腰;他走路有点外八,鞋子大、步伐也大,还走得快,永远风风火火,跟他走在一起我得一路小跑,像要去救火。
阿杜是坐在我们后面的女生,她老拿圆珠笔戳兔子的衬衣,“兔子,这道题怎么解?你跟我说说呗。”兔子学习好,是一枚妥妥的学霸,而我是“战五渣”。这时候兔子就笑眯眯地转过身,给阿杜画辅助线。我说也给我讲讲题目呗,他白了我一眼,“这种题目你还是放弃为妙,把前面的基础分抓牢。”
文理分班时,兔子很苦恼——文理科他都擅长。如果最后不是选了“高精尖”的生物工程专业,没准他现在和我一起写诗呢。
不过做文艺青年,他确实不会有出路。同一个寝室里,大伟不让他碰吉他,我不让他动口琴。上完晚自习,他只能趴在寝室阳台上,干嚎两嗓子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”。但对面不会有女孩看过来,倒是校长办公室会收到投诉。兔子五音不全,有一次文化节汇演的时候,我们班男生合唱《永远不回头》,他一人跑调,几乎带偏了所有人,还坚持一吼到底。
那时候我正在追隔壁班的女生,而兔子在追隔壁学校的女生。他学我写信,想要鸿雁往来。兔子总是拉着我,研究那个女生的回信,试图找到女生喜欢他的证据。
但事与愿违,兔子很快“失恋”了,一头扎进习题集里。最后,兔子去了一所985大学,我去了“双非”报到。我们联系得依然勤快。春天来了,兔子的心又开始萌动。他跟我说,他喜欢上了他们班一个小家碧玉的短发女生。
他把人家堵在校门口表白,得到的结果自然是“对不起”。兔子有点沮丧地回到了实验室。当我再得知他的消息时,他已经去德国念书了。
大学毕业的时候,我开始在网上写博客,间或发表些文字作品。兔子是评论区的常客。有一年他回上海,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,说等硕士毕业后准备继续留在德国读博士。我突然感受到我们之间的差距,热闹的房间安静了下来,气氛略尴尬。
后来阿杜问我兔子怎么样了,我真惭愧——自他读博以后,我们再没有频繁互动。只晓得,他在德国进了人人皆知的企业,结了婚,生了一个女儿。
我记得最后一个跟兔子打篮球的夏天,我们躺倒在阳光底下,大笑地聊着梦想和未来。当时我们无比投缘,后来就逐渐没有了交集。当年的几个好友曾约定毕业二十年后回母校团聚,一眨眼就到了约定之期,我因工作出差去了北京,兔子仍留在了德国,我们都在微信群里留言说抱歉。
从前没有手机、微信,我们总是很容易就能找到要找的人。如今我们有微信,能视频通话,居然真实地断了联系,就像水滴消失在水里。
按我过去的理解,有些人出国以后没回来,要么是因为过得还不够好,要么是因为过得实在太好了。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——我们不过是各自过着平凡的生活,体味着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。这大概也应了王小波的那句: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。
尽管时光一去不返,我还是会在心里默念:远方的兔子——祝你一切安康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