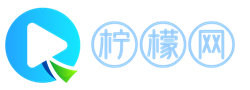无论现代意义的“大众”概念何时形成,大众始终是一个顽强的表述主体。从古老的民歌、地方戏到现今的卡拉OK、广场舞,大众的活跃身影从未缺席。很大程度上,传媒历史的逐步进化,间接证明了大众的巨大吸引力。甲骨、青铜、竹简、纸张、平装书、报纸、电视、互联网,传媒的演变线索始终围绕一个主题持续延伸:接纳更多的大众共同参与。如何表现?表现什么?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,大众的强烈吁求汇聚为演变的巨大动力。这种动力同时传送到文艺形式。古代文学之中的词、曲、章回体小说无一不是对大众的积极响应。如果没有大众的推波助澜,五四时期白话文的崛起与兴盛是不可想象的。
现代意义的“大众”概念具有纷杂的脉络谱系。无论是劳苦大众、工农大众、群众、人民这些不同的称谓,还是西方文化之中的mass与popular,大众概念背后隐藏多种观念的角逐。概括地说,人们可以解读出三种涵义:一、仅仅表示人数众多,一个中性的形容;二、带有明显的贬义,譬如蒙昧的乌合之众或者缺乏独立见解的庸众;三、正面的肯定性命名,譬如工农大众、革命群众。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历史发展的意义上肯定了大众的巨大作用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,大众才是真正的历史创造者。当然,这时的大众不仅表明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,更重要的是阶级的身份特征。阶级被视为社会构造的基本单位,同时成为鉴别大众性质的基本范畴。“劳苦”大众、“工农”大众以及他们身上的革命性质,恰恰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肖像。少数垄断财富的剥削者发号施令,旁若无人,然而,这些财富由大众的双手创造出来。大众必须充当历史的主人公——这个事实长期遮蔽于层层叠叠的传统观念背后,而文艺则应发挥其“还原真相”的作用。五四新文学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“大众文艺”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,重新描述大众的历史地位,归还他们应有的文化权利——表现与被表现。1942年,毛泽东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论述了大众的构成、文艺的表现对象与接受主体、艺术家的任务以及大众喜闻乐见的传媒与文艺形式等一系列问题。如果说,文学史上的“老妪能解”显现为一种艺术个性或者一种艺术风格的选择,那么,大众文艺的倡导基于新型的历史文化构图。这时,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大众文艺不仅包含“人民”的历史地位认识,而且广泛涉及大众传媒与文艺形式。
很大程度上,“新大众文艺”的提出是与“新传媒时代”联系在一起的。文艺家已经察觉,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大众传媒正在发生重大改变。围绕互联网的虚拟空间,文字与影像符号、图片、声音汇聚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区域,并且催生出众多富有活力的文艺形式。更为重要的是,技术革命带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革命。互联网果断撤除各种多余的限制,大众纷纷作为表述主体坦然进入这个空间:“‘新大众文艺’是一场创作者的革命。创作者无须再像纸媒时代那样,苦心孤诣地构思写作,等待发表。新时代的所思所想,或键盘输入,或音像录制,须臾之间,心中块垒得以纾解,脑中所想得以倾吐。无论身份,不论阶层,门槛消弭,圈子打破,人人皆可为作者,老少皆可成博(播)主。”二十世纪上半叶,多数工农兵大众还无法自如地使用文字叙述自己的见闻,然而,当代的大众业已今非昔比:“现在不同了,义务教育普及,劳动者文化水平普遍提高,劳动者参与文学有了更广泛的基础。这个时代,几乎每一个劳动者都能拿起笔,记录他们的生活,表达他们对生活的感受、情感和认知。”(《延河》编辑部:《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》,《延河》2024年7月)这个意义上,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大众传媒恰逢其时。
“新大众文艺”之“新”来自历史聚焦的转移
按照上述观点,“新大众文艺”首先对纸媒文化拥有的编辑出版体系发出挑战。对于空前活跃的大众说来,编辑出版体系仿佛退化为一种桎梏。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发表作品,编辑出版体系并非纸媒文化固有的技术性障碍,而是来自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。从审美趣味到叙述技术,大众必须接受精英观点的筛选。当然,哪怕是察觉到编辑的保守、狭隘、囿于小圈子趣味,哪怕陈陈相因的出版规则抑制了大众的自由发挥,这仍然是一个需要严肃论证的问题:纸媒文化的编辑出版体系真的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吗?
必须承认,精英/大众之间的张力仍然构成许多文化生产模式的内在结构,只不过大众介入的环节不同。科学技术领域,大众无法介入实验室的专业研究或者编写软件程序;大众作为消费者守候在市场的出口,市场的评价仅仅以反馈意见的形式重返研发与生产环节。事实证明,这种循环仍在产生正面效应。体育竞赛是另一种精英/大众的互动范本。尽管大众对于许多体育项目相当熟悉,但是,社会成员的体能与技能存在种种落差。体育竞赛遴选机制的意图是,期待落差的弥补促成大众的提高。显而易见,精英/大众的循环不可避免地形成等级的区隔,形成主从之分或者中心与边缘对于大众的压抑。“新大众文艺”甩下精英/大众的文化生产模式,展示理想的文化平等状态。这时,种种传统的理论预设不得不面临考验。“文艺”是不是某种边界清晰的专业?这将成为一个有待商榷的学术问题。大众能否突破精英构成的防线,作为历史的主人公进驻“文艺”?这涉及文化权利的重新分配。
大众踊跃地写出自己的故事——与“新大众文艺”相辅相成的另一个观念是,作为读者,大众同时对于自己的故事高度关注。他们的双手正在创造历史,这种自信是将目光转移到自己身上的理由。大众可能快乐豪迈,可能痛苦悲伤,但是,他们不再卑微渺小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——甚至自己也忽略不计。许多时候,大众遗忘自己的存在从而对那些异己的“远方”表现出超常的兴趣,例如帝王将相、宫闱秘事,或者武侠神魔、玄幻穿越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讨论“大众文艺”的时候,许多左翼批评家已经尖锐地指出这一点。生活在别处,大众将拯救苦难的希望寄托在“远方”的救世主身上,从未意识到自己身上隐藏的力量。迄今为止,这些廉价的安慰性想象仍然汇聚在各种“通俗”的类型文学领域,占有很大的市场。“新大众文艺”与各种类型文学分道扬镳,大众的觉醒是不可或缺的前提。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,武侠神魔的惊险奇幻,这些情节带有多数人无法涉足的传奇性——传奇制造诱惑乃至迷醉;相对地说,“新大众文艺”充满烟火气息,甚至琐碎絮叨、家长里短,但是,这时的大众不再是英雄背后无名的平均数,他们的面容、经历、独特的悲欢浮现出来,跨出抽象的背景进入舞台中心。打开闸门,喧哗的日常生活景象一拥而入,堂而皇之地占用“新”的名义。“新大众文艺”之“新”来自历史聚焦的转移。
从“传统”“市场”“大众”等维度深化对命题的思考
从五四时期“人的文学”“平民文学”到一个世纪之后的“新大众文艺”,这一条历史线索始终与三个问题相互缠绕,此起彼伏,或者针锋相对,或者遥相呼应:一、文艺形式与传统;二、市场的意义;三、大众的范围。
数千年的文艺史,遗存了相对独立的文艺形式体系。形形色色的文艺形式来源不一。一些文艺形式源于民间的自发创造,继而获得文人雅士的加工、修饰、完善;另一些文艺形式来自专业人士之手,例如诗歌之中繁杂的象征系统、电影镜头剪辑、交响乐谱曲,如此等等。这些文艺形式凝聚为传统,逐渐形成表述的规范,并且承担聚焦审美愉悦的功能。相对于个别文艺家,这些文艺形式是独立的、先在的,必须刻苦研习才能熟悉与掌握。追溯各种文艺形式的起源可以发现,它们曾经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显示出强大的表现力,这种表现力恰恰是它们得以固定、独立、获得承传并且晋升为传统的重要原因。然而,对于“新大众文艺”说来,这是珍贵的遗产还是多余的累赘?无视《诗经》、楚辞、唐诗宋词的诗学积累,抛开王羲之以来的书法传统,从零开始的诗歌与书法能够跑多远?另一方面,相当一部分文艺形式与大众生活存在距离:古代文人雅士的情趣、感想以及农业文明的意象与大众的粗犷、风风火火或者现代社会的车水马龙存在距离,来自口头文化、纸媒文化的表述方式与互联网为中心的符号体系存在距离。“新大众文艺”多大程度地接受或者拒绝先在的文艺形式?这不仅涉及文艺家的认定,而且涉及审美标准的认定。“新大众文艺”的积累必将形成自己的文艺形式。这些文艺形式被视为传统文脉的延续,还是重铸另一种性质迥异的新型艺术语言?古往今来,相似的问题一直化身为各种理论命题盘旋在文艺史上,“新大众文艺”再一次要求理论的明确表态。
进入现代社会,文艺之所以脱离“我手写我口”的原始状态,文艺形式的规范仅仅是原因之一。与文艺形式紧密相连的是传媒体系。传媒决定文艺的符号品种。声音、文字、影像分别对应舞台、纸张与屏幕。多数传媒是人工产品,并且按照一定的模式运行。如果说,古代的传媒体系时常由王公贵族或者宗教势力掌控,那么,市场与商业愈来愈多地介入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。无论是报纸、书籍还是电影或者电视节目,大众传媒的运行需要相当高的成本,同时可能获取高额利润。现代工业为文艺的生产与传播制造了一个崭新的平台,电影或者电视的导演、演员、主持人以及企业经营者赢得的报酬是古代社会无法想象的。这个意义上,商业集团对于大众传媒的操纵乃至垄断丝毫不奇怪。商业的力量不仅影响作品的传播范围,而且干预作品的内容与文艺形式。商业与市场对于大众传媒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,但是,二者的逻辑并非“新大众文艺”的轨迹。无论是纸媒鼎盛时期还是电视机主导的年代,人人皆为作者只能是一种虚幻的渴望,多数人无法负担书籍出版或者电视节目录制的成本与技术要求。“新大众文艺”的希望由互联网点燃——个人的手机操作足以完成文艺生产的全部流程。尽管如此,人们没有理由无视另一个事实:互联网并非远离商业与市场,而是二者激烈争夺的中心地段。手机屏幕背后的商业博弈从未停止。“新大众文艺”如何栖身于市场与商业的环境?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浮现。
“新大众文艺”之“新”不仅可以修饰“文艺”,还可以修饰“大众”。任何一个历史时期,当“大众”成为一个赢得赞誉或者遭受贬抑的社会群体时,另一些社会群体通常成为相对的参照。相对于劳苦大众或者工农兵大众,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或者书斋里的知识分子无形充当了“他者”。当然,各种社会群体的相互参照具有清晰的历史烙印。“新大众文艺”提出的同时必须考虑,谁是现今的大众?如果说这个问题过于笼统,那么,另一种反向的概括或许相对精确:谁不是现今的大众?诸多社会学文献表明,知识分子与企业家业已纳入现今历史阶段的大众成员,共同汇入历史的创造。这种认知与“新大众文艺”是否一致?文化的意义上,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界限的改变意味着什么?
“新大众文艺”的提出显示了特殊的文化敏锐,现在是展示这个命名内部理论涵义的时候了。醒目的命名转换为深刻的命题,理论涵义的充实是最为重要的条件。